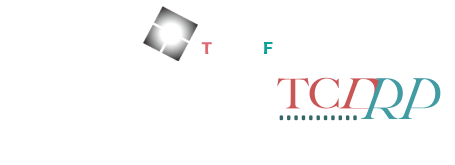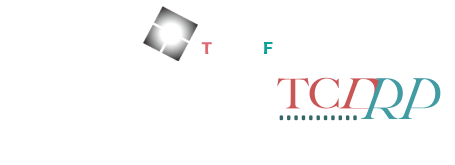|
【影片旁白】
在一、兩百年前,交通不發達,工作生活的用具還簡單,而全靠勞力的那個時代,凡是遠渡重洋,離開家鄉到偏遠的地方去開拓荒地的人,他們平時除了身體上的勞苦之外,在心靈的深處也一定是非常非常寂寞,所以拓荒的人比一般人更容易想家思鄉的呢。也只有處在這樣的背景的人,他們的想家思鄉之情才顯得更為生氣,然而生氣的懷念頻頻激起心靈的嘆息,久而久之,連貫了這種從心底深處冒出來的嘆息聲,也就串成歌,然後把思鄉的情景編謠入歌,於是歌謠就形成了。
我們所熟悉跟喜愛的這支恆春民謠「思想起」也就是一、兩百年前,從大陸到恆春來開荒的祖先,由他們思鄉的心聲所匯起來的。這一支純樸優美的思想起,除了當時唱慰著他們勞苦寂寞的身心之外,流傳到今天也成為我們民族音樂的模樣。現在的人己經不知道一支心靈的歌聲是用血汗鋪起來的,以為歌曲是看電視,聽唱片就得了。所以思想起的歌名,也被誤傳為思想枝,以為歌詞也只有一個,就是唱娶了大太太,就得該再娶姨太太。如果我們把今天在電視裡面唱的思想起,唱給來恆春開荒的祖先聽聽,不知他們躺在棺材裡會有什麼感想。
台灣的地方雖然不算大,但是各個地方都有一些與人不同的風俗習慣,拿恆春嚼檳榔的風俗來看,就比起台灣別的地方普遍得多,並且方法也有所不同。一樣的從大陸福建、廣東移民到台灣來,定居了之後,竟然會發生某些風俗習慣的差異,這就不能不注意當地的人文,或是自然的環境。根據歷史的記載,中國江南一帶雖有吃檳榔的風俗,但是未普遍成為一般人的習慣,至於台灣南端的排彎族,他們可以說是吃檳榔的士族,當時移民到恆春半島來的祖先,跟原居民的風俗差異,開墾期間常發生衝突跟仇殺械鬥的現象。漢人婦女為了避免被殺害,外出工作時打扮成山人婦女,頭纏布巾,嘴嚼檳榔,並且用頭頂物。沒想到當時只是為了保全性命,勉為其難的偽裝,如今卻變成恆春人風俗習慣的一大特色。
從這點我們更能看出文化的同化作用是彼此互相的關係,問題是彼此間影響的多少罷了。在恆春,年上三十歲以上的婦女,大部分都喜愛檳榔,甚至於穿著摩登的小姐,也有人嚼檳榔。這裡更叫外地方人感到驚奇的是,在恆春連6、70歲沒有牙齒的老人也不放棄嚼檳榔的習慣。問題很簡單,如果把牙齒看作嚼檳榔的工具,沒有牙的老人可以把堅硬的檳榔先用工具搗碎,然後放進口裡,這不就得了嗎。
恆春的檳榔跟台灣其他地方的檳榔不一樣,這裡大部分的檳榔叫「番仔青」,比平時看到的「仁青」大,嚼起來醉人。外地的人吃了番仔青會頭暈,恆春人沒有番仔青就覺得不過癮。有一個恆春的年輕人把家裡的老人接到台北來奉養,結果老人放棄了台北豐富的物質生活,又回到恆春去。人家說,他為什麼不懂得享福呢?他說,台北什麼都好,就是沒有番仔青。到了恆春半島,隨處放眼望去,到處都可以看到綠色的長葉舉著天空的瓊麻,這種普遍的景象,就像我們到嘉南平原隨處都可以看到稻田是一樣的。
幾十年前的農業社會,一般人如果要是說,某某人有多少財產、有多富有的話,在產米的地方就是說,某某人有多少多少甲田。在恆春半島的地方,他們就不這麼說,他們一定是說某某人有多少甲地的瓊麻園,如此可見瓊麻在恆春半島的農業地位。事實上也是如此,瓊麻在此地佔所有作物面積的百分之80以上。瓊麻的葉子榨出的纖維大約有60公分到100公分長,因為瓊麻在海水中的耐腐力特別強,所以被人拿來造漁船建築上,跟路上用的粗細大小的繩索。其實很多人早就都是跟瓊麻熱烈的握過手的老朋友呢。只是一時叫人想不起來罷了。你參加過拔河比賽嗎?對了,拔河的那條粗繩,就是瓊麻編的。
瓊麻雖然在此地占了作物面積的百分之80以上,這也意味著這裡有很多直接靠瓊麻生產工作維生的人。這些麻農的生活自然而然的被瓊麻起伏不定的價格牽動著生活的情緒。這幾個月來瓊麻的價格起伏很大,最低的時候一公斤2塊錢,最高也曾經高達一公斤12塊。自從人造纖維的成本降低以後,瓊麻的價格就一直被壓下來了。但是1973年的中東戰爭演變成能源危機以後,人造纖維的原料短缺,瓊麻的身價也一下子看高了許多。目前一公斤是9塊6,比起前些年的2塊錢實在是好多了。看來瓊麻的景氣似乎好轉過來,麻農的生活也可以因而得到改善。但是能源危機為瓊麻抬高了身價,同時也由能源危機所引起的國際性通貨膨脹,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一個人,不受這種經濟風暴的影響。如果今天瓊麻一公斤9塊6是好價錢的話,且看看瓊麻人的這些補燈打袍,也無法跟瓊麻並駕齊身吧。
瓊麻的價格能夠提高,都是麻民所渴望的,但是當瓊麻跌到一公斤2塊錢的時候,他們也無法放棄賤賣勞力的工作。他們唯一的一個補救辦法,只有拉長工作時間,動員全家所有大小的人力,增加產量,增加斤兩,希望能夠多掙一點工錢。這裡更叫人不安的是,他們常常為了加快工作,而把榨液機的開口從X的5公分放到10多公分,也因為如此為生活焦慮的工作著,常常在坐月子進入榨液機的時候,就被拖進機器的滾刀處理裡面去了。在恆春地方經常會遇見很多這種連住在一起,XX給社會的男女老幼。
一整片的瓊麻仁,不管是在海邊,或者是在山坡地,一片望過去都是很好的風景。但是外地到恆春觀光的遊客千萬小心,晚上想走進瓊麻仁約會的話,除非能夠攜帶兩套盔甲穿上,不然不要太冒險哦。
當然恆春地方在宗教信仰上,還是跟台灣其他地方一樣,絕大部分都是佛教、儒教、道教三教並奉的,所以在恆春一帶,仍然跟其他地方一樣,到處都可以看到廟宇,所不同的是在恆春一帶的廟宇,沒有台灣其他地方的廟宇宏偉。不要說在此地找不到像北門鄉、南鯤鯓的王爺廟,北港的朝天宮,或是木柵的天宮廟,就像一般小鎮的主母廟的規模廟宇都找不著。這個理由很簡單,任由廟宇都是當地的信徒蓋的,如果當地的經濟不發達,老百姓的經濟情況也是比較差,這跟漁村的媽祖廟來看漁村的經濟情況是一樣的,愈發達的漁村,媽祖廟蓋得愈大。
這是在恆春白砂海邊的小廟,在恆春一帶提及古山廟茄苳王沒有人不知道,甚至於外地的漁船,遠到南方澳的漁船,行駛此地的海面時,還得遠遠的朝古山廟朝拜。茄苳王之所以聞名,據說不能夠生育的夫婦,或是為生男育女困擾的人,只要虔誠的來燒香進拜,大部分都能如願以償。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也跟目前家庭計畫推行委員會的宗旨,並不衝突吧。茄苳王曾經只是廟會的這棵百年老茄苳樹,後來被附近居民,傳聞一些應驗的靈蹟之後,才蓋了古山廟。初秋是茄苳結子的時候,在偏遠的鄉下沒有什麼零嘴可吃,酸澀的茄苳子也就變成他們不花錢的零嘴了。
這是在恆春鎮東南約2公里遠的赤牛嶺山腰上的鎮南宮,在恆春地區也算是一所香火興盛的古廟,可是它的規模一直是這樣小。其實不管廟寺的大或小,如果能處在幽靜的鄉野山間,自然形成一片平和之氣,使來朝拜或是來遊勝的人投入裡面的時候,心情也自然恬靜下來。只要來過赤牛嶺鎮南宮的人,一定會享受到這樣的心靈靜地,而令人似乎覺得可以從此回溯到古老的中國傳統似的。
誠然,在台灣廟宇的大小可以看出當地的經濟情況,然而在恆春半島,也就是說西從東港,東從台東縣的尚武以南,都落在所謂落山風的勢力範圍,因此沒有一所古老的建築是高大。當每年的晚秋到第二年春夏之交,整個恆春半島都落入落山風的侵襲範圍,也成為落山風的季節。在這段時日,通常都是風聲蕭蕭,塵沙滾滾,風力強烈的時候往往跟中型颱風的風勢一樣。為了抵擋這種風勢,這裡老式的民房都蓋得比較矮,最顯著的是他們的窗戶隔得特別小。尤其是朝東北方向的更是要護板的設備,另外屋脊也開了一排風口,來減低對風的阻力。
有人認為恆春地區經濟蕭條,落山風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但是在恆春地區的作物,比其他地方的蟲害少,人也比較健康,比較能夠克苦,此地的牛也比較壯,追問起這個原因,當地的老人說,這都是落山風考驗出來的。在恆春地方,上百年的古老建築物,除了鵝鑾鼻的燈塔,也是光緒元年的建物,恆春鎮的古城是碩果僅存的祥瑞古物。由於古城早已失去了實用價值,經過光緒34年的大颱風、民國34年盟機的轟炸、還有48年8月15的6級大地震,使一座173點5丈的城牆,1834個城垛、城台、城樓、炮台全部毀壞了,現在很難得的還留下來東南西北的四個城門。有很多外地來的年輕觀光客,當他們抬頭仰望著城門,像面對百年老怪物發聲疑問說,做這種城幹什麼?那麼恆春人會笑一笑的告訴他說,讓你們來觀光啊。
在我們中國任何地方,這種文物似乎是太多了,也就不叫人珍惜。其實在很多先進的國家,把自己的文物當作寶貴的文化財產,好好的保護起來。外國人來不來看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作為給我們後代的人,來溫習祖先的奮鬥史,不是一件很值得的事嗎?現在登上上一個世紀破敗不堪的城門,想想當年為了16萬7千390兩銀子的古城,令人覺得落山風刮得特別帶勁。
有一個現象連本地的人還找不出答案,那就是伯勞鳥跟落山風兩者之間的默契。伯勞鳥過後,落山風就準時來恆春打卡上班,一季之中可以說是全存備了。每年落山風來臨之前,就出現成千上萬的伯勞鳥,這種鳥平時是看不到的,到這個時候就出現。沒有人知道牠們是從哪裡來的,有人說從菲律賓來的,但是菲律賓的鳥類專家卻說,菲律賓沒有這種伯勞鳥。伯勞鳥的出現,在一年之中也給此地的老人跟小孩子帶來一點生活上變化的情趣,伯勞鳥未來之前,他們就做好了許多Y字型的竹竿彈簧的圈套,在野地裡到處的豎起來,尤其瓊麻仁是設圈套最好的地方,因為伯勞鳥的習性是不喜歡成群結隊的。每一隻鳥都喜歡獨樹一枝,所以當伯勞鳥看到有高桿豎在野地,牠就自然的飛去停憩,就在牠停憩的剎那也就是牠失足落入圈套的時候。把一失足成千古恨拿來比喻伯勞鳥這種遭遇,是最恰當不過的,因為牠的失足,沒有一隻能夠逃過變成烤鳥的命運。
活的伯勞鳥一隻2塊錢,烤熟的一串兩隻10塊,這個價錢是近幾年來到恆春觀光的遊客增加了以後才有的。不管怎麼樣,這對喜歡野味的觀光客而言,是世外桃源真正的物美價廉的價錢。在伯勞鳥的季節,楓港車站一帶,伯勞鳥的焦味也真正發揮了令遊客聞香下馬的作用。
當伯勞鳥去了,跟落山風一起來的是老鷹。恆春人在傍晚注意老鷹棲在哪棵樹上,到夜晚就帶著手電燈跟弓箭把牠射殺。這種老鷹在一隻10塊的利誘之下,被搜刮去剝製標本,賣給日本之後,現在也快絕跡了。
恆春的這些,在我們物質文化緊迫之下,即將成為過去。那麼,當我們再禁不住的哼起恆春民謠「思想起」,或是偶爾聽到,那已經不是早前來恆春開墾的移民對故鄉的懷念了,而是我們遠離了我們古有的一些傳統,迷惘著對我們過去的時間傾訴著懷念罷了。
|